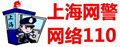□薛 涌
从假期、工作时间等一系列硬数字可以看出,美国的工作环境,造成了生活与事业的“自相残杀”,两者难以兼顾。被卡在中间的女性,往往首当其冲地被牺牲。这种局面,有制度上的问题,更有文化上的问题。
美国创立之初到整个十九世纪,基本上是个清教国家。二十世纪经过了多元文化的洗礼,清教的影响依然相当大。这种清教精神,和自由放任的美式个人主义相结合,缔造了一种对超人的崇拜:成功者都是因为他们自己有非凡的品性。他们能够克服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、肩负常人难以支持的重担,和任何社会条件、特别是国家的政策和支持都没有关系。这种“自我造就的人”,缔造了狂热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。这样的人物本身,也处处意识到自己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。他们的行为举止中,一个重要的面向就是要显示自己能够胜任别人承受不了的工作量。这些年美国极端体育在成功人士中的崛起,就是这种自我认同的一部分:我为什么能成功?跟我跑跑马拉松就知道,我能把任何人都拖垮。我有你想象不到的精力。《华尔街日报》的个人生活版,几乎每周都有几篇某某CEO的训练日程。如今胖子越来越难当企业领袖。没有看家的运动强项,在生意街仿佛就不那么风光。
美国的职场,往往是这种极端体育在办公室的演绎。Anne-Marie Slaughter 特别提到当年《纽约时报》的报道:里根政府的财政主任 Dick Darman,总要给人们一种印象,他是在办公室里战斗到最后时刻的人。甚至他回家时,也要办公室点着灯,并且把自己的西装留在椅子上,给人一种他还没有离开的幻象。他事后解释说,把西装留下是因为回来穿上更方便。但他一贯的心理战记录显示显然是另有原因。
上行下效,在美国的职场,特别是上层职场,盛行的是一种几乎不睡觉的敢死队式风气。华尔街的人早就声言: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睡觉时间,根本没工夫回家,就睡在办公桌底下。更多的时间等于更多的工作、更大的附加值,这几乎成了共识。大家比的,是谁最早到办公室,谁最晚走,谁永远钉在那里、随时准备在星期六上午11点进行面对面的工作会晤。美国进步中心最近的统计显示,每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的专业人士比例,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持续上升。
在德国,老板要把下班时间从5点半延长到6点,公司的工作委员会马上就发话:晚半个小时下班,有些职工回家吃完晚饭赶不上音乐会了。工作委员会可以很容易否决CEO的决定。而工作委员会都是职工选举出来的。而在美国,你口口声声什么“工作与家庭平衡”的人,就会被视为职场异类而遭到排斥,甚至丢工作。大家都那么献身,为什么你要抱怨,就你有家庭?甚至连办公室的同事也不会同情你。
在 Anne-Marie Slaughter 看来,工作超时经常是不得已。压力就是那么大。但在美国的职场上,这种超时加班几乎成了一种行为艺术,大家都在比,哪怕并没有什么效益。特别是在网络时代,明明许多在家可以完成的工作,一定要在办公室里做,给同事和老板看。这让我想起一位在日本公司当了十年建筑师的朋友的观察:“日本人下班不走,在办公室里泡着,其实什么效率也没有,就是一起混混而已。最后大家一起喝酒,喝一晚上,醉得吐一地,这叫工作?他们这样折腾到午夜12点以后才回家,不是真加班赶任务,而是要表示自己是以公司为家、每天都不想回去。你真干活快,给同事造成压力,有关人士会来修理你一番。”Anne-Marie Slaughter对美国职场的观察,颇有些类似之处。以她的经历,超时工作往往降低效率,但这是办公室的文化。
2009年,Monitor Group的一位女老板委托哈佛大学管理学院进行调查研究,看看本公司内是什么因素促进或者妨碍了女性雇员在工作中的表现。最后的调查结果显示,公司那种“永远在发动状态”,而不管对职工影响的文化,是最大的问题:客户永远是第一位的。有时熬夜确实管用,保证按时完成任务。有时则是盲目给员工加码,而不考虑这些额外负担是否产生效益。管理层似乎保有着一种职工的时间很便宜,可以随便用的理念。乃至在加班没有带来附加值的情况下也要加班。女性,特别是刚刚生儿育女的女性,要在这样的企业文化中生存,谈何容易?(作者为美国萨福克大学副教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