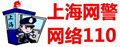顾 筝
周明怎么都没有想到,他已经这么拼了,“惊喜”还是变成了“惊奇”。
“之前看过新闻,知道这里队伍总是排得很长,我计划凌晨三四点到,心想总能买到了吧。为了今天早起,昨晚特地9点多就上床了。早上四点赶到这里,没想到只能排到后面那个转弯角。没办法,只能出100元向黄牛买个略靠前的位置。”周明原本的计划是赶上头一批月饼出炉,买去给同事们当早餐吃。但即使从黄牛那里买了靠前的位置,排到他时也已近11点钟,“惊喜”的早饭变成了“惊奇”的午饭。
这是一条神奇的队伍,淮海路上的光明邨大酒家前,队列中的人永远计划赶不上变化;这是一道奇特的风景,映衬着车水马龙的弄堂里排队的人蜿蜒不绝,刮风下雨雷打不动,老面孔、新面孔,买熟食、买鲜肉月饼、买点心……而现在临近中秋,鲜肉月饼窗口前的队伍更是在弄堂里绕出了长长一个圈。为了让更多的人买到月饼,店家早就实行了限购,玻璃窗上贴着告示:自9月1日起每位顾客限购60只,敬请谅解。
光明邨的鲜肉月饼是用平底锅煎焖,一锅排放60个,一共5个锅。由于排队的人力成本很高,队伍中99%的人都会买足份额,即使自己实在不需要那么多,也会有人打探到了消息过来拼单:“阿姨,侬不买足我帮侬一道拼好伐?”一批出炉的月饼只能供应5个人,一个小时只能满足10个人的购买量,当然,这只是理论上的购买速度。
“啥月饼?吃了能长生不老啊?”一个爷叔路口经过,看到这么长的队伍不免发出评论。
“我也没吃过啊。”这一天拔得头筹的穿红色POLO衫的爷叔说:“是我朋友指名要吃这个牌子的月饼。我昨天就来过了,来得晚,根本买不到,今天早上我3点多就到了,一看,排到转角去了。哪能办?200块摸出来给黄牛,我跟他反复确认过的,这个位置能保证我第一个拿到。”
同样凌晨3点多到,不舍得买黄牛票的牛仔布短袖衬衫老伯站在转角处的位置忿忿不平:“我们3点多到,他们前面一个人占十个位子,就只好站到这里了。”这位头发雪白的老伯指着队伍最前面的20多个位子抱怨,“除了零零星星几个是自己带着板凳、干粮前一天下午五六点就来排队的人,其他都是伊拉(黄牛)霸牢额”。老伯自己是一早骑着助动车从普陀区赶过来的,其实他去年就曾来过,当时觉得队伍太可怕,悻悻然地回去了。今年他还是决定来排这个队:“是买给屋里厢长辈吃的,我都这个岁数了,长辈是吃一年少一年。其实啊,光明邨老早名气又不灵的喽,不过现在啊,其他地方都做得越来越差,它维持以前的水平么,就算是进步了。”“是的呀,现在食品都不让人放心……”排在老伯前面的一个阿姨附和道,两人的话题就这样慢慢从老品牌“堕落”开始抽离了黄牛。
和老伯一样,除了黄牛,排队来买月饼的大多是为了送人。“自己吃才不来排这个队呢?吃饱了。”一位戴眼镜的阿姨说,“女儿要送人。她要上班,只有我们退休的人来排队了。”她和爱人是一起来的,两人轮换着排队。排在队伍前面的一家三口是为数不多自己来“人肉排队”的人,“家里长辈欢喜吃呀,我们每年都来的,一年就一趟,这份心意无论如何要尽的。去年是晚上十一点多来,今年特别吓人,昨天下午五六点就来了,还好拿了张沙滩椅好眯一会。明年我们也找人买个位子算了,这样排队太伤身体了。”年轻的女子说。而年长的男性一直有点闷闷不乐,看到前面队伍有点骚动,他说:“你们一个位子到底还有多少人要插进来啊?我们也是昨天晚上就来排队的!”让他动怒的依然是黄牛。同行的中年女性拍拍他的背,让他不要多响,免得发生争执。阿姨的息事宁人是有道理的,这条移动缓慢的队伍冲突却在时时爆发,喉咙最响的基本是黄牛。黄牛也分几个派别,有在弄堂内开饭店的本地人,也有外地人,冲突音量最大声通常来自黄牛斗黄牛,虽然都是老面孔,一旦觉得对方抢了生意,骂起来不饶人。
排队的人群躁动不安,阴晴不定,有一位穿着短袖衬衫的爷叔静静地坐在自带的小椅子上,他是这一天的幸运儿,他的手中拿着一张白纸,上面打印着:今日购买月饼最后一位。这是光明邨的营业员根据这一天的生产量,大致依据排队人数后发给他的纸,这也是为了提醒后面来的人不要再排队了。
幸运爷叔是早上六点半来的,他一直尽职地举着这张纸。可是在他身后,队伍还在延续着。一个排在队伍里的短发阿姨说出了这些排队者的心声:“这是按每人买60只算的量,万一人家没买足呢。我们总归不死心的呀。”
这是一条神奇的队伍,有人为尽心,有人因贪心,一锅锅地道传统的“上海味道”串起人来熙往,串出人情冷暖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
我,就在神奇的队伍中,从早上7点排到10点,终于挪动了30公分。